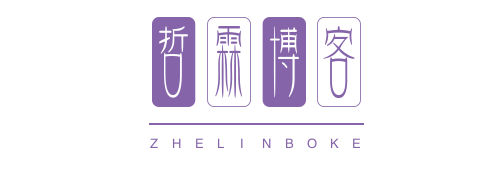原标题:“弘进轮”舟山获救背后:国际航运船员“下船难”困局
 8月11日,东悦轮船员举牌求助。受访者供图
8月11日,东悦轮船员举牌求助。受访者供图
8月12日,“弘进轮”(GRAND PROGRESS)的最后9名船员还在做着下船前的准备。从7月30日开始,船上20名船员里,陆续有13人先后出现发烧等症状。有的人反复发烧,严重者还出现呕吐、失去味觉嗅觉等情况。
弘进轮最终在舟山港获救。8月9日,舟山方面确认16名船员核酸检测阳性。当天晚上,11名船员被点对点闭环接至定点医疗机构救治,其余症状较轻和无症状船员暂留船治疗等待,待船员管理公司后续换班船员到岗后轮换。
在航运界人士看来,弘进轮在被困几天后就能获救、短期内实现人员顺利下船,在疫情肆虐的当下,这就是“最好的结局”,是一个“罕有的成功案例”。
与之相对照的,是国际航运的船员难下船、难换班的问题,从疫情开始后存在至今。
 8月13日,弘进轮船员将部分待销毁物品清理到甲板上。受访者供图
8月13日,弘进轮船员将部分待销毁物品清理到甲板上。受访者供图
一天清理出十余吨需销毁物品
第一批11人下船后,弘进轮留下了9名海员进行清理、消杀等工作。16名替换人员则在就位待命,等船上准备就绪,即可换班。
8月11日上午,周念安和留在船上的船员们开始对整船进行打扫。留在船上的9人里仍有5人核酸检测阳性。不工作的时候,船员们各自呆在舱房,工作的时候仍然需共处一室。11日这一天,他们一起做了大半天消杀工作,清理出来十余吨需要送到岸上销毁处理的物品。
周念安已经两天没有好好吃东西,虽然船上米面油都有,但他不会做饭,舱房里最后一包方便面,是他备下的应急口粮。快要下船了——他这么盼望着,下船之前,这一包应该够了。
作为一艘巴拿马籍货轮的最低配备,弘进轮此次需要至少招聘共计16名海员接替工作,但由于20名船员16名核酸检测阳性的消息在航运圈里人人皆知,在船舶管理方发出招聘广告后,应者寥寥,弘进轮船员证实,目前船方开出高价招聘新船员。8月11日,弘进轮的船管方、天津跨洋国际船舶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接受采访时称,已招到十五六名船员,正在待命。
 8月11日,弘进轮船员对船只进行消杀。受访者供图
8月11日,弘进轮船员对船只进行消杀。受访者供图
开不进的港口
弘进轮不是第一艘被困住的船。就在周念安目送同事们下船时,300公里外的东悦轮(EASTERN DELIGHT)正在求助。
东悦轮是利比里亚籍,轮上19名船员中12人是中国籍。包括二副刘腾在内的5名中国船员,原计划要在某港口下船换员。“船东和船员公司都同意,但被船舶代理告知该港口目前无法安排船员休假。”东悦轮发出的求助信里称,咨询多家当地船舶代理寻求换班方案,“均因疫情期间手续无法办理为由遭到拒绝。”
这不是第一次遭拒。刘腾说,他们5名船员最初准备于七月底八月初在广东某港口换班,但被代理告知,由于疫情形势紧张,无法办理船员换班手续。
根据《2006年海事劳工公约》,海员服务一般不得超过11个月。通常情况下,国际航运的船员连续工作8个月左右会下船休息。疫情前,港口如果发现有船员超过劳工公约规定的期限,可以强制遣返让公司换人。
但疫情改变了一切。据中新社报道,直到2021年1月,全球仍有超40万海员滞留海上,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已经连续工作达17个月,远远超过业内及监管限制工作时间。
船员们习惯把在海上航行的日子叫做“坐水牢”。动辄在海上漂泊数月,极考验人的心理承受能力。“疫情前还能在靠岸的时候下船走走,疫情后全球没有任何一个港口会允许船员上岸。”刘腾说,这意味着从踏上甲板的那一刻起,船员就开始面临合同期内的至少8个月的“刑期”。随着疫情带来的各种变数,曾经可以估算的“有期徒刑”,现在变成了“无期徒刑”。
刘腾的船员已经开始出现失眠的状况。长期在船无法上岸带来的焦虑,以及不知道期限的“水牢”带来的压力,让他们感觉煎熬。
8月13日,东悦轮获得确定消息,船上的5名船员可以在南通港下船换班。
码头困境
困局中,港口方直接成为船员的对立面。
“是真的,现在(大部分港口)不让外轮船员下船。”某国企码头生产作业负责人王天平和舟山港某码头生产作业管理人员郑泛都明确承认这个现象的存在。郑泛表示,自己所在的码头“从来不让(外轮船员)下船”。王天平说,内贸轮船的管理相对比较宽松,船员只要持有检测报告等港口当地政府要求的手续,大部分情况下还是可以办理换员手续,但外轮基本不允许上下人员。
“对码头企业来说,换员跟码头关系不大,可防疫的主体责任却在码头身上。”王天平说,“码头只要发生一个确诊病例,立刻封锁,然后全员核酸检查3次以上,直接接触确诊病例的三班人员拉到指定隔离地点隔离14+7天。我们隔壁码头遇到一艘外轮卸货,离开后发现船上有船员新冠阳性,整个码头都封了,到现在还没开。”
王天平认为,对于疫情防控来说,这样的严管“无可厚非”:“有人上下就多一个风险点,一旦出事还存在追责的问题,而且每封一天都是损失,还会影响在客户心里的印象,以后就不到你这里来了。”
疫情下船员换班手续的繁琐也让港口一方感觉头疼。2020年五月左右,王天平所在的码头有且仅有一次允许外轮在此换员。王天平说,硬着头皮办这件事是因为当时船舶上的“特殊情况”,“船员已经在船上呆了一年没有下过地,船公司反馈说心理都出了问题,开始有暴力倾向。船已经靠岸,他们在船上出事我们也要担责任。”
国内某大型港口船舶代理公司工作人员说,疫情前,换员是极普通平常的操作,没有任何难度可言,基本按流程打报告即可,疫情后,换员难度大幅度提升,“难归难,最后还是能走下来。只是时间流程被拉很长,基本上船到锚地前半个月就得跟我们敲定,然后发文件过来,审批流程至少一周。”
采访中,多名外轮船长和船舶代理表示,上海、青岛等大型港口,成功换员的可能性较高。“小一些的港口,有些没有换员的能力,比如没有完全隔离的条件。”一名船舶代理称,每个港口的收紧程度都不同,如果是松散型的港口,有时甚至不同的码头也有不同的规定,“比如这个码头可以下,那个码头就不行。没有统一的标准。所以最后能不能下船,一个是和地方执行操作方式有关,另一个和地方疫情发展密切相关。”
 8月11日,大丰轮发出施打新冠疫苗申请书。受访者供图
8月11日,大丰轮发出施打新冠疫苗申请书。受访者供图
疫苗难题
换员问题还直接影响着船员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弘进轮上20名船员,只有轮机长打过疫苗,他也成为所有感染者中“自愈”情况最好的一个。周念安也很想打疫苗,但他11个月前登船时,国内的新冠疫苗尚未正式推出,疫情发生后,港口都不允许船员下地,对于船员来说,随时出海的特性让他们能够按时按地接种两针疫苗变得极为困难。以上种种,造成相当数量的外航船员,身为高风险人群,却完全“裸奔”。
记者了解到,东悦轮上的12名中国船员里,5人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本次下船,他们的另一项要务就是去打疫苗。
8月11日,大丰轮(DATO FORTUNE)船长马卫俊带领船员,签了一份《大丰轮船员施打新冠疫苗申请书》发送给船舶代理。大丰轮是巴拿马籍货船,船上23名船员都是中国人,14人未接种疫苗。申请书中明确希望能施打“一针式”疫苗。“安排防疫人员施打或者组织专车去岸上接种点都行。我们愿意支付由此引起的相关费用,我们愿意承担由于我们施打疫苗而可能感染其他人员的一切法律责任。”截至记者发稿时止,大丰轮的申请尚未获得回应。
外航船员出海,一般两三个月才能回国一次,严格按照间隔一月打两针疫苗几乎不可能实现。今年5月,中国船东协会向国家卫健委、交通运输部提出为船员接种“一针”新冠疫苗请求,拟在11个口岸城市提供。
根据巴哈马海事局(BMA)一项调查的结果, 全球87%的海员仍在等待接种第一支新冠肺炎疫苗。也就是说, 坚守在新冠肺炎疫情前线的海员中只有13%接种了疫苗。
等待破局
关于船员轮换的问题,国家六部委曾在2020年4月出台过一份《关于精准做好国际航行船舶船员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就中国籍船员换班问题提出要求:国际航行船舶入境后,计划换班下船的中国籍船员经海关检疫无异常且核酸检测阴性后,自船舶驶离上一港口满14天、健康记录显示连续14天及以上正常的,在办理换班入境手续后,港口所在地人民政府应当给予便利。
根据《2020年中国船员发展报告》,截至 2020 年底,我国共有注册船员 1716866 人,其中国际航行海船船员 592998 人。2020 年 4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完成境内港口中国籍船员换班 14.7 万人次。
但在现实执行中,大部分船员甚至走不到“海关检疫”的步骤。“约束性文件没有强制效力,在疫情压倒一切的情况下,最后决定权还是在地方政府和港口手里,造成现状的原因就是相关方不敢担责任,‘一刀切’。”采访中,多名船长这样认为。
山东交通学院国际商学院陈超教授认为,要解决现状,需要出台能落地执行的管理细则,以及加强边防防疫功能。作为港口方管理人员,王天平也在这场困局中觉得困惑和两难,“这不是某个公司或者码头造成的,是整个大环境的问题。要解决它,换班的程序和方式应该有个统一的规范。把要求固定下来。”
多位航运界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表示,航运界在等待一个疫情期间外轮船员下船的标准程序,即使它可能复杂,但“好过没有”。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周念安、王天平、郑泛为化名)
文 | 新京报记者 杨雪 实习生 郭莉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