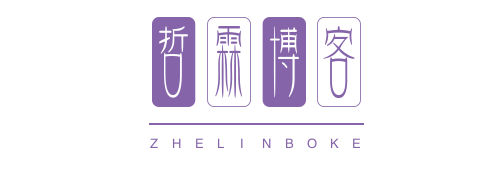原标题:寻找泰坦尼克号中国幸存者
 制作团队在下川岛留影,脚下是当年方荣山离家的地方。从左至右依次为首席研究员施万克、制片人罗彤、研究员李大川、导演罗飞。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杰/摄
制作团队在下川岛留影,脚下是当年方荣山离家的地方。从左至右依次为首席研究员施万克、制片人罗彤、研究员李大川、导演罗飞。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杰/摄
 纪录片团队在海外拍摄。受访者供图
纪录片团队在海外拍摄。受访者供图
 研究员李大川看望方荣山的后代。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杰/摄
研究员李大川看望方荣山的后代。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杰/摄
 方荣山寄给家人的照片。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杰/摄
方荣山寄给家人的照片。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杰/摄
 方荣山写给妹妹等家人的信。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杰/摄
方荣山写给妹妹等家人的信。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杰/摄
 泰坦尼克号上6位中国幸存者中的4位。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杰/摄
泰坦尼克号上6位中国幸存者中的4位。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杰/摄
电影《泰坦尼克号》开始时,镜头追随男主角杰克扫过三等舱通道,一位留着发辫的中国人正拿着词典寻找舱室。巨轮沉没后,他趴在一张漂浮的木板上,用广东话喊“我在这里”。
杰克和露丝的爱情是虚构的,这个木板上的中国人不是。
当爱好研究海洋历史的美国人施万克(Steven Schwankert)找到他的导演朋友罗飞(Arthur Jones),说想拍一部关于泰坦尼克号的纪录片时,后者兴趣寥寥,“泰坦尼克号很主流,还有什么可以发现的。”
施万克告诉罗飞,泰坦尼克号上有8位中国乘客。
他俩在中国生活超过20年,施万克记得1998年电影《泰坦尼克号》上映时,他去北京东单电影院观影。那时流行盗版碟,电影院票价比较贵,座位也不舒服,BP机的呼声总响,“但还是有那么多人去看,还去看第二次。”连不会英文的中国大妈都能唱出原版的主题曲《我心永恒》。
2012年电影3D版重映,中国内地的票房近10亿元,几乎占此片海外电影票房的一半。2019年,为吸引游客,四川大英县一家公司宣布投资10亿元打造一艘1∶1的泰坦尼克号仿制品。
尽管中国人对这艘“漂浮的宫殿”充满热情,但很少有人知道三等舱里有8位同胞,并且有6人幸存。
在海边长大的施万克说,“如果人们只知道一艘沉船,那就是泰坦尼克号。任何能修改或是增加这个故事的一部分,都算很成功。”
一开始,他以为这是个关于沉船的故事,吸引他的是解密的过程。后来他发现,“沉船就是一大块钢铁”,船上人的故事才让它变得有意义。经过五六年艰难的调查之后,施万克向100多年后的人们重新介绍这6位被遗忘的中国幸存者。“而泰坦尼克号并不是他们人生中最大的苦难。”
六个名字
寻找“六人”的原始资料只有6个名字,它们写在旅客名单里:Ah Lam、Fang Lang、Chang Chip、Lee Bing、Cheong Foo、Ling Hee。
“这是粤语吗?还是闽南话?”施万克感到疑惑,为什么这些100多年前的中国名字全是两个字?每一个读音都能对应好几个汉字。纪录片团队很早就放弃了Cheong Foo的故事线,因为叫这个名字的人实在太多了。“Ah Lam”则在历史里一直被错误地记录成“Ali Lam”。
在上海一家办公室里,这6个名字分散地写在一块白板上,关键信息一条一条填上去,围绕在名字周围。研究员分布各地,上海四五人、北京有一个小团队、美国两三人、英国两人、加拿大两人——其中一位是在脸书上看到消息而加入的家庭主妇。
施万克对沉船故事着迷,但面对孤零零的6个名字,他感觉研究之旅就像抽奖,最终可能一无所获。
一位研究员在美国查找各个档案馆和图书馆,浏览1912年4月和5月沉船时的报纸,几千页里找不到采访这6人的记录,尽管当时美国已经有二十几家中文媒体。
泰坦尼克号有700位幸存者,在美国华盛顿的中心地带,曾矗立着纪念雕像。出生于英国的导演罗飞说,幸存者至少在自己的国家都小有名气。他小时候有个年迈的邻居在泰坦尼克号上活了下来,随便上网一查,就知道她何时出生、有几个孩子、她在船上的经历和她人生的故事。其他幸存者都有类似的“待遇”,除了那6个沉默的中国人。
“如果你对中国幸存者没有什么特别兴趣,研究他们很难。”施万克说。
2018年,纪录片团队委托了一家叫中华家脉(My China Roots)的公司,寻找6人的踪迹。这是一家帮助海外华人寻根的公司,曾促成一位得克萨斯州的华人女士与广东的远方亲戚团聚,也替一位新加坡华人在英国利物浦找到了他从未听说过的同父异母的妹妹。
创始人李伟汉出生在荷兰,他的祖先在200年前离开福建后,这个家族在海外生活了7代。除了名字、生日时的长寿面和皮肤的颜色,李伟汉成长过程中没有其他中国元素。直到一次回国,他才理解“认祖归宗”对他心理的长远影响。
通常情况下,李伟汉的委托人都是想要寻找祖先的后代,但寻找这6人不同,既要寻觅祖先,也要找到后代,“与其说我们是回到过去,不如说是在努力前行。”
那时,施万克团队已经查出这6人受雇于英国商船,公司打算送他们到纽约,再转船到古巴,最终将热带水果运回英国。他们因此才踏上泰坦尼克号。在巨轮撞上冰山后,6位中国幸存者被送上岸不足24小时,就立即踏上了另一艘去往古巴的船只,继续漂泊之旅。
幸运的是,李伟汉的团队在伦敦的国家档案馆发现了船员名单。上面记录着水手的出生地、上下船的时间以及曾在哪些船上工作过,甚至在6人中找到4人的中文名字,还发现了一些照片。
有的船员名单里写着他们在英国的住址,那是利物浦老旧的唐人街,纪录片团队跑去那里时,很多建筑已经不在了。
研究员还发现,躲过了海难的Chang Chip,没躲过肺炎,只过了两年,他就在伦敦去世。他埋在伦敦的东南边,墓地上添了新冢,没有留下墓碑。
在英国的研究员说,追踪6人是个令人着迷的经历,尽管带着悲伤色彩。看着陈旧的中国船员照片,研究员想像着他们百年前的生活:在巨大的蒸汽船的锅炉房里工作,远离家乡和亲人,总在漂流,没有永久的地址,“对许多人来说,这一定是一种孤独的生活。”
从船员名单中记录的信息里,研究员大致拼凑出6人离开泰坦尼克号后的行踪,他们运送水果回到欧洲,再去北美,再回欧洲,又到北美,有的人的名字出现在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的船上。
“有人问我,为什么你们拍纪录片跑了那么多地方。”施万克说,“因为他们(6人)跑了很多地方,我们被推到那里。”
Ah Lam是6人里年纪最大的一个,“将近40岁,但照片看上去有50岁。”施万克说。在船员名单里,他的名字总是排在第一个,研究员猜测,他很可能是6人的领头人,经验多些,英语还可以。
Ling Hee脸上有道疤,这让研究员很快确认了他的身份。他最后一次出现在资料里是1920年,他从印度下船,自此销声匿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商船水手从海军退役,原本填补他们空缺的中国水手就显得多余了,许多人被秘密遣返。
Ah Lam的轨迹消失在亚洲某个地方。“你想想,你做了几十年水手,突然把你送到几十年没有生活过的地方,工作也没了。”看着百年前的照片,施万克感慨道,“就好比我回美国3周,签证突然被取消,我在美国又没有工作,我的东西都在中国,那怎么办。”
方荣山和Fang Lang
方国民出生在美国,不大能讲普通话,喜欢用枪猎鹿,有自己的一块地。他经营一家餐厅,住在中产社区。有一天,方国民收到一封来自中国的邮件,“你认识泰坦尼克号上的Fang Lang吗?”
“那是我的父亲,他的名字不是Fang Lang,是方荣山。”
方国民印象里的父亲总是西装笔挺、打领带,手上戴着一个镶金边的玉戒指,他习惯沉默,常常微笑看着儿子。
1894年,方荣山在广东省台山市下川岛的村子里出生。台山是著名的侨乡,在下南洋、闯五洲的鼎盛时期,甚至有“美国华侨半台山”的说法。台山话在北美唐人街曾被视为中国的“国语”,称“小世界语”,与“大世界语”英语相对。
如今台山百年前的建筑上,还写着:才华胜过华盛顿,武略赛过拿破仑。
方荣山1920年进入美国,那一年他26岁。 61岁,他才拿到美国公民身份,马上结婚、回乡探亲。他娶了20多岁的妻子,生了两个儿子,很快离婚了。晚年,他在餐厅做服务生养活自己。
方国民记得,父亲带他去租房,开门的是个高个子白人,嘲笑他们是“黄狗”,方荣山一拳打在那人脸上,那时,他已经70岁了。
他的一生几乎都生活在唐人街,四周是旧楼,衣服和拖把挂在外面。华侨们虽然离乡多年,但仍保留着中国的生活习惯,在家里摆关公像,贴领袖画像,挂黄历。
那个年代,许多初到美国的华人选择开洗衣店。一位台山同胞讲述自己的经历,“我在矿场每个季度剪发一次,别人叫我四季头,后来积聚几个钱,便改行从事洗衣业,本钱不用多,只要有块小小工作间,一块搓衣板,一个熨斗便可以了。”
这些在家乡不事洗衣的男人觉得没面子,常瞒着国内的亲戚,在家书中,他们把洗衣店称为“衣衫馆”。
方荣山每个月都给台山的家人寄银信——一种带有汇款的家书,现已被列为世界记忆遗产。他在信里分配着一笔笔10美元、20美元,重要的信息用红笔写,“可能从下川岛出发的那一天,他脑子里就装着一个想法,要照顾家人。”施万克说。
朱红品是方荣山胞妹的孙子。“我奶奶的生活都靠大舅公寄回来的钱。”那时在农村养个猪,两年都不长膘、上不了市。
朱红品记得,方荣山从美国寄来水果蛋糕,装在蓝盒子里,“后来吃过的所有蛋糕都比不上。”64岁的朱红品住在一间拥有大落地窗的复式建筑里,遥想当年生活。那个盒子被保留了10多年,搬家时才扔掉。
上世纪70年代,朱红品曾替家人跟大舅公通过信,方荣山的信中经常有一句“世界大战难免,希望世界和平。”那时方荣山已经很老了,总是在信里说着鼻子不舒服、眼睛生病了。
在台山收藏华侨物品的关翌春有上千封银信。1950年,一封从美国旧金山寄到台山的银信里写道:“吾相信中国各地尚有困难,一时未能办到,料政府有办法,祈各人安心。”1952年,“华侨在美国不甚自由,亦仅仅能维持生活耳”“料我国迟数年,发展工业农业等,相信多华侨回国过太平之日也。”
如今,在家乡台山,银信变成了电子转账。
关翌春说,像方荣山一样能踏上美国的土地已是幸运。再早些时候,许多台山人被“卖猪仔”,关在舱底运往各地做苦力,生病了就扔下海。一张照片里,华工的辫子挂在绳上,全身赤裸,等待检查身体。“好像蚂蚁一样”。
1859年由澳门开往古巴的船只触礁而沉,船长水手乘小艇逃生, 850名华工全部死亡。
美国太平洋铁路建筑时,万名华工作出极大贡献。当东西两段接轨,于1869年举行庆祝典礼时,华工没能参加。这些人在美国被称为“中国佬”“支那佬”,在家乡却被尊称为“金山客”“金山伯”。带回“金山箱”,塞得越沉越满,越是荣耀。
Lee Bing很可能也往家乡寄过钱,“他的一生算是成功的。”施万克说。
Lee Bing的踪迹出现在加拿大的一个小镇上。他是6人中唯一公开谈论过船难的幸存者。他在加拿大开了一间咖啡馆,常端着牛奶送给街边玩耍的孩子。
方国民从未听父亲讲起泰坦尼克号或是船难,他甚至不知道父亲做过水手,母亲也不知道。但方荣山胳膊上有一个水手常见的水果文身,方国民只见过两次。
曾与方荣山通信的后辈朱红品,听奶奶念叨过大舅公“乘大船撞冰山”的事情,“一个老太太没有文化,唯独这件事记忆了几十年,一定是触动很大。”
究竟“大船”是不是泰坦尼克号,纪录片团队研究了那段时间撞冰山的所有船只,发现只有两三艘,且多为小船,方荣山很可能就是泰坦尼克号上的Fang Lang。
下川岛寻人
方荣山的故乡下川岛在南海之滨,热带典型植物环绕,一处沙滩已被开发为景区。山的另一面,本地人保持着平静的生活。一片人迹罕至的沙滩上,海浪呼吸起伏,100多年前,方荣山就是从这里坐船远行。
虽然方国民坚信父亲方荣山就是Fang Lang,纪录片团队仍在寻找更结实的证据。
研究员李大川的祖籍也是台山。他爷爷那代去了美国,父亲在美国出生。因为寻找方荣山的历史,已过中年的李大川回到家乡,“我去了至少30个村子。”
李大川常穿整洁的衬衫,保持儒雅的派头,寻找方家后人仿佛寻找自己的过去。每每去村里打听,他总结出经验,时间选在午饭后,地点是每个村都有的风水树,老人家喜欢坐在下面乘凉,李大川远远看到他们,就笑着打招呼。
村民总是热情地回应着外来者。施万克记得,他们有一次敲陌生人的门,一位赤膊男人应声开门,看到眼前架着麦克风、摄像机,还有外国人,男人爽快地都请进门。“如果是我,肯定锁门,报警。”施万克笑着说。
2018年,纪录片团队在下川岛找到了方荣山的侄孙,面对镜头,他忽然念起方荣山写在信里的诗:“天高海阔浪波波,一根木棍救生我,兄弟一起有几个,抹干眼泪笑呵呵。”
诗附在正文旁,字迹清晰,概括了方荣山的经历,也是证明他是Fang Lang的重要证据。
在美国旧金山湾一片花木葱茏的小岛,建筑物上出现一块块整齐的汉字。它们跟方荣山的诗很像,“美例苛如虎,人困板屋多,拘留候审多制磨,鸟入樊笼太折堕”。
当载着泰坦尼克号幸存者的轮船抵达纽约港时,正是美国《排华法案》施行的时期,中国的底层劳工不被允许进入美国,商人、学生等除外。
天使岛是移民等待被遣返的处理站,企望从这里进入美国的人,常常要等待半年时间,接受轮番审问,证明自己的身份。问题有“家里米缸放哪”“从大路到你家房子门口要走几步”,稍有错误,即被遣返。
纪录片团队找到研究天使岛的华人学者杨月芳,她70多岁了,满头白发,有力地背诵着中国人在百年前留下的苦痛诗篇。有人甚至不堪折辱而自尽。
制片人罗彤在现场听着,眼泪滚了下来。“我完全感受到当年华人进入美国的心情。”她为拍纪录片入境美国时,被移民官拦下,进入等候室,被严厉询问。“我才等了三四个小时,那些人等了三四个月。”
如今,天使岛已成为美国移民历史博物馆。《排华法案》于1943年底废除。
施万克形容,寻找6人的过程就像拉一条丝线,能拉下一点就是新发现,如果断了就只能算了。
导演罗飞记得有一张著名的照片是幸存者在海难次日早晨拍下的。如果能在救生船里看到Fang Lang的脸,再与方荣山的照片对比,无疑是最有力的证据。
罗飞用放大镜仔细看着网上下载的照片,很难看清楚。他搜索到英国的一家档案馆里有原始照片,立即付费买下,等了几个月,终于收到一个大信封。他急忙打开,看到背面的档案馆标志,兴奋地翻过来,发现是个很小的版本,比网上的还模糊。
不过最终,纪录片团队还是找到了有力的证据。
Fang Lang的船员名单信息显示,他在1920年登上一条从法国开往美国的轮船,船舶停靠在纽约港,离开的时候,Fang Lang不见了,那一天是9月15日。
方国民在父亲的移民文件里找到了他入境美国的时间——1920年9月15日。几乎没有别的可能了,Fang Lang就是方荣山。
抹干眼泪笑呵呵
儿子方国民感到疑惑,泰坦尼克号这样重大的人生经历,方荣山为什么不告诉家人。
1912年英美报纸上虽然没有采访到6人,但从其他乘客的口中,“中国佬”被说成乔装女人,混进救生船偷生,还有人说他们藏在舱底。
施万克找到北京一所国际学校,请学生们花了一年时间1∶1制作出救生船,让他们坐进去。他想用物理学解决历史问题,究竟中国幸存者有没有可能藏在舱底。
实验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施万克对那时的媒体和政府调查感到恼火,“一些最明显的或者一定要问的问题,为什么当时没人问?”
“如果用2021年的眼光看,想活着,不是坏事,这是人权。”施万克说,但他也理解当时一些人的反应,“你的丈夫带着你和孩子到新的国家,最终他没有上救生船,船上却有几个中国人,你当然很生气。”
当初的污名仍笼罩在现代人的头上。纪录片团队曾找到另一个后人的线索,他看到拍摄的片段哭了,但仍不想讲出身世。
“那个时代的中国人,能不说就不说,心里放着很多秘密。”导演罗飞说。
1912年的那个夜晚,6人中有4人登上C号折叠救生艇,一人在泰坦尼克号沉没之际登上最后一条救生船。方荣山和他的两个朋友没能上船,落入水中。他靠一块木板等来折返的救援。
那艘船的指挥者罗威实际已经把船划开了,但很快改了主意,又返回。方荣山被拉上救生艇,有个女乘客揉着他的胸脯,其他人揉着他的手和脚,他睁开了眼睛,说着人们听不懂的语言。船上的一位幸存者后来讲述道,这个亚洲人很快恢复了力气,替水手划起桨。指挥者罗威说,“如果我有机会,我宁可救他这种人6次”。
导演罗飞认为,方荣山没有告诉家人这段经历,很可能是为了保护他们。从1920年进入美国,到1955年拿到合法身份,方荣山过了35年非法移民的生活。他有七八个名字,处在灰色地带,缺乏安全感,也习惯了不去讲自己的故事。
“父母用不说话的方式保护下一代,下一代却以为不说代表不爱我。”罗飞说。有的华人后代直到父母去世,才懂得他们,而另一些人,始终无法理解上一代,也失去了机会。
远在台山的朱红品,有时能体会大舅公方荣山为何沉默。改革开放之初,朱红品开着旧拖拉机两天两夜到珠海讨生活。没有固定住所,就住在路边工地留下的破房子里,挡风不遮雨。
他建在路边的修理厂因为城市建设而被拆除,又逢父亲生了场大病,他穷到“2万元卖我这条命”。
“人有的时候熬的苦超出他的负荷,好些事情就不想讲了。”他猜测着大舅公的心境,“可能他压抑自己压得太重,太苦太累。”
台山人大多记得父辈移民的艰辛。关翌春的主业是经营一家翻译社,做出国中介。一个家族,往往一个人先出去,再把一家人带出去。有的女人希望通过婚姻出国,40多岁还没嫁,等到老,等一个出国机会。
如今,在台山城中心,华侨留下的骑楼建筑里每天进行着现代商业活动。建筑的外观有古希腊的柱廊、古罗马的拱券,与中国民间的梅兰竹菊、福禄寿喜结合。无论外形多西式,骑楼的最高层往往供奉着神龛,镌刻着家风和祖训。
在2019年,台山市有163万海外华侨华人,国内的常驻人口有95万。但出国的热潮在衰减,关翌春发现,最近5年,生意不好做,许多年轻人不愿意出去。
出海之地
施万克猜测,方荣山的沉默还有另外一种解释:“他没觉得这是特别了不起的事情。我坐船,船沉了,我幸存了,那又怎样,我还得活着,我还要赚钱。”
1912年,踏上那艘豪华的游轮时,18岁的方荣山行李里装着两双靴子,6件衬衫,半打领子和领带。他很有可能计划着在不久的将来,和两位朋友在俄亥俄州开一家公司,成为商人,合法地生活在美国。“年轻的方荣山要赚钱,要成功,这是他的梦。”施万克说。
随着巨轮与冰山的致命撞击,方荣山的两个朋友沉于海底,他靠一块木板等来救援,除了生命,一切都没了。
“他最终也没有成为很有钱的人。”施万克说。方荣山开过洗衣店和餐厅,过了两三年倒闭了,又开一家,又倒闭了。但他耐心地等了35年,一直寄钱回家,帮助亲友。
现代人已经很难理解那种坚持了,施万克说。在拍纪录片的过程中,他经历了亲人离世、调查毫无进展、素材严重缺乏,几次想放弃,但想一想,还是一直往前走,“你也可以抓住那块木板”。
电影《泰坦尼克号》里,趴在木板上的中国人,是好莱坞华裔数码影像制作设计师林凡客串的。得知纪录片即将拍摄,林凡第一个表达了支持。
电影导演卡梅隆愿意担任纪录片的监制,并说服好莱坞同意纪录片使用《泰坦尼克号》的片段。他们还征得了每一位出现在镜头里的演员同意。
在西方人的视角里,泰坦尼克号是值得宣扬一生的印记。指挥救生船的罗威的孙子,家门口挂着纪念铭牌,他的家里像博物馆,有照片、有报纸、有遗物。“罗威像个泰坦尼克号的王子”,热爱海洋历史的施万克说,他能见到罗威的后人,十分激动。
方国民跟着纪录片团队,来到罗威孙子的家里。100多年前,一个人的爷爷救了另一个人的爸爸。罗威孙子的身体不大好,但爱开玩笑。他说爷爷有次在家附近的小河里,从大船跨到小船时摔了一跤,第二天就上了新闻,“泰坦尼克号幸存者又幸存了”。
临别时,罗威的孙子把爷爷的照片送给了方国民,他说,“我们找到了彼此,这个圆终于合上了。”
不久后,纪录片团队收到邮件,罗威的孙子因病去世了。
如今在方国民的家中,摆着一个泰坦尼克号的模型,船的一侧是罗威的照片,另一侧是父亲方荣山。
方荣山一生默默无闻,官方的文件里看不到他的身影,家族故事里也没留下多少话语。109年过去了,他的儿子也许能骄傲地讲出父亲的故事了。
1986年,方荣山在美国去世,终年92岁。那一年,美籍华人李远哲获得诺贝尔化学奖。那一年也是国际和平年,60位华人歌手演唱了歌曲《明天会更好》。
今年4月,纪录片《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在国内上映,票房无法跟商业片抗衡。制片人罗彤说,很多人以赚不赚钱来评价制片人,她不这么想,把一帮人凑在一起,做成一件事,人生有一次这样的经历足矣。
纪录片上映后,制作团队回到了台山市下川岛,3年前面对镜头背诗的方荣山的侄孙中风了,躺在床上,起不来身。制作团队用电脑给他播放纪录片片段,告诉他“全世界都知道你念的诗”。老人嘴里说着听不懂的话,眼角有泪。
制片人罗彤还记得3年前,摄像机数据卡掉在了方荣山当年离家的沙滩上。第二天,团队所有人返回寻找,每步走两厘米,一点点摸索。最终,近视的导演发现了它。望着被海水涨潮退潮无数次的地方,罗彤感到,冥冥之中,这块土地的人想让他们把故事讲出来。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杰